

有人說復刻錶是影子,永遠追著真品的腳步。
直到我在鹿港小巷的「時光邊角」工作室,看見陳姐將七塊廢棄復刻錶拆解重組。
當她將那枚意外流出的真品貝母錶盤,鑲進拼裝錶殼時,月光正落在指間細微的裂痕上。
「碎掉的東西,」她摩挲著錶盤邊緣的缺角,「有時反而能拼出真模樣。」
台北城冬夜的雨,細密而陰冷,帶著一種黏膩的穿透力。我拉高外套領子,低頭鑽出台中高鐵站,濕冷的風立刻像冰水般灌進頸項。手機螢幕上,一個模糊的地址導引著我,在鹿港曲折如迷宮的紅磚窄巷裡穿行。導航幾度失靈,最終停在一條僅容一人通過、連招牌都幾乎被兩旁老屋簷水浸蝕殆盡的小巷口。巷子深處,一點昏黃的光暈,像黑夜裡固執不肯睡去的螢火蟲,微弱地亮著。門邊一塊小小的木牌,字跡已被風雨剝蝕得難以辨認,勉強認出「時光邊角」四個字。
推開那扇嘎吱作響、彷彿隨時會散架的舊木門,一股混合著陳舊機油、金屬冷冽、以及某種極淡雅花香的氣息,奇異地融合著撲面而來。這氣味,與台北老周店裡那股濃重沉鬱的機油樟腦味截然不同,帶著一種被刻意打掃過的、屬於女性的細緻痕跡。店內極小,僅容轉身。牆壁被整面頂天的木架佔據,架上並非整齊排列的名錶,而是無數大小不一的透明塑料格,裡面分門別類地盛放著難以計數的細小零件——齒輪、螺絲、軸承、游絲、各式各樣殘缺或完整的指針、錶盤碎片、甚至孤零零的錶冠和底蓋……像一座微縮的機械廢墟博物館,在頭頂一盞光線柔和的工作燈照射下,閃爍著冰冷而沉默的光澤。
陳姐就坐在房間中央唯一的工作檯後。檯燈的光圈將她籠罩。她看起來五十歲上下,身形清瘦,挽著一個乾淨俐落的髮髻,幾縷不聽話的銀絲從額角垂下。鼻樑上架著一副精緻的玫瑰金邊放大鏡,鏡片後的眼神專注得像在進行一場精密的手術。此刻,她手中鑷子的尖端,正穩穩地夾著一枚比米粒還細小的寶石軸承(jewel bearing),小心翼翼地將其歸位到一枚拆解得只剩骨架的機芯夾板中。她的手指纖長,關節處卻有著長期用力留下的細微變形和薄繭,動作精準、穩定,帶著一種渾然天成的節奏感,彷彿她指尖流動的不是時間,而是某種沉默的詩句。
我,阿誠,在「TW手錶網」筆耕二十年,自以為看遍台灣鐘錶業的眾生相。從後火車站批發市場的喧囂洪流,到金融海嘯後復刻錶工藝的畸形躍升,再到電商時代真假混戰的亂局,我記錄過產業的脈動,剖析過技術的流變,也見證過無數老師傅在時代齒輪下的堅持與掙扎。然而眼前這一方天地,這座由無數被遺棄的「殘骸」構築的殿堂,以及這位在廢墟中安靜「復活」時光的女匠人,卻讓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震動。這裡沒有真偽的激烈辯證,沒有對原廠血統的頂禮膜拜,只有一種近乎禪意的、對器物本身生命週期的尊重與延續。我報上姓名和來意,提到是業內一位相熟的機芯供應商林老闆輾轉介紹而來。陳姐抬起頭,透過放大鏡片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平靜無波,像是早已洞悉一切,只微微頷首:「林老闆提過。坐吧,地方小,別介意。」聲音溫和,帶著鹿港一帶特有的軟糯腔調,卻有種不容置疑的沉穩力量。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工作檯上一塊攤開的深藍色絨布吸引。布上,散亂地放置著幾塊明顯來自不同時期、不同「血統」的復刻勞力士女裝日誌型(Lady-Datejust)零件。一隻28mm的錶殼,邊緣有幾道明顯的磕碰凹痕;一枚自動陀上刻著「Seiko NH05A」字樣、顯然是拼裝上去的細小機芯;幾根長短不一的指針;幾枚鑲嵌著廉價水鑽的羅馬數字時標;還有一枚……我的呼吸微微一滯。
那是一枚勞力士經典的「鑲鑽」三角坑紋(fluted)外圈。但吸引我的不是它,而是被陳姐暫時放在外圈旁邊的一枚錶盤。那錶盤的材質……在檯燈柔和的光線下,它呈現出一種無法複製的、流動的虹彩!深藍的底色上,細膩如絲綢般的天然紋理蜿蜒流淌,隨著光線角度的微小變化,折射出從深邃的紫羅蘭到幽靜的墨綠、再到點點碎金般的光澤變幻——這絕非仿品常用的廉價塗料或印刷貝母紙!這是真正的天然珍珠母貝(Mother of Pearl)錶盤!而且,更令人心驚的是,在錶盤邊緣靠近三點鐘日曆窗的位置,有一道細微卻清晰的弧形裂痕,像是遭受過一次不為人知的撞擊。
「陳姐,這盤……」我忍不住開口,聲音因激動而有些發緊。作為一個浸淫此道多年的編輯,我太清楚這意味著什麼。真正的天然貝母盤,因其材質的稀有性和加工難度(極易碎裂),成本高昂,幾乎不可能出現在中低端的復刻錶上。而這枚盤面上,在六點鐘時標下方,那個鐫刻得極其精細、線條銳利、立體感十足的皇冠標誌(Rolex coronet),更是真品的鐵證!它怎麼會流落到這裡?又怎麼會帶著傷痕?
陳姐停下了手中的動作。她輕輕拿起那枚貝母盤,指尖極其溫柔地撫過那道冰冷的裂痕,彷彿在撫摸一道陳年的舊傷疤。她的目光落在那些流轉的虹彩上,眼神變得有些悠遠。
「九年前的事了,」她開口的語調很平,卻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回憶的漣漪,「那時,我還在大肚山腳下,一家專做『高級復刻』的代工廠裡。」她的話,瞬間將我拉回那個台灣復刻錶工藝試圖衝擊「頂級」天花板的瘋狂年代。
彼時,我正為「TW手錶網」撰寫一系列深入產業鏈的報導。市場對「亂真」級復刻的渴求達到頂峰,價格也水漲船高。陳姐所在的工廠,接到的正是當時最炙手可熱的訂單——復刻勞力士女裝日誌型,要求極高:必須使用天然貝母錶盤,鑲嵌「真鑽」外圈(當然,所謂「真鑽」在業內約定俗成指的是等級較高的莫桑石或立方氧化鋯,但光澤和火彩必須接近真鑽)。
「廠裡進了幾片瑞士過來的……嗯,『特殊渠道』的貝母盤,」陳姐的措辭很謹慎,但我們都心知肚明,這些盤面的來源往往游走於灰色地帶,可能是瑕疵品、報廢品,甚至是……「多出來」的部件。「薄得像蛋殼,美得驚心動魄,但也脆得一碰就碎。」她的指尖無意識地沿著眼前這枚盤面上的裂痕描摹,「打磨鑲嵌的過程,師傅大氣都不敢喘。我負責最後的鑲鑽外圈組裝和QC(品質檢驗)。」她的聲音裡透出一絲當時的緊張。
然而,命運的惡作劇總在不經意間降臨。就在一批成品即將下線交付給香港大客戶的前夕,一場突如其來的地震襲來。震級不大,卻足以讓工廠那並不算穩固的貨架劇烈搖晃。「嘩啦啦——」一陣令人心臟驟停的碎裂聲響起。陳姐衝過去,只見幾隻已裝配好、等待包裝的成品女裝日誌型,從貨架上跌落在地。其中一隻,錶鏡碎裂,更可怕的是,那枚珍貴的貝母錶盤,在錶殼內撞擊變形,邊緣赫然裂開了一道細長的口子!
「老闆的臉,當時就綠了。」陳姐的語氣帶著一絲苦澀的嘲諷,「那批貨,一隻開價十幾萬台幣!裂了盤,整隻錶就廢了!他抄起那隻摔壞的錶,像丟垃圾一樣狠狠砸在牆角。」碎片四濺。那枚帶著裂痕的貝母盤,像被遺棄的孤兒,從扭曲的錶殼裡彈跳出來,滾落在滿是油污的地板角落,虹彩蒙塵。
「我把它撿了回來。」陳姐的聲音很輕,卻像錘子敲在我心上。「老闆發現了,暴跳如雷,指著我鼻子罵:『撿這破爛幹嘛?能賣錢嗎?留著招晦氣!』」她頓了頓,彷彿還能感受到當時撲面而來的唾沫星子,「他說得對,在那個只計算成本和利潤的工廠裡,一道裂痕,就判了它死刑。」那場衝突的結局,是陳姐被當場開除。她收拾自己寥寥無幾的工具時,悄悄將那枚帶著傷痕、沾著灰塵的貝母盤,裹進手帕,放進了口袋。「它不該被那樣對待。」她對我說,目光再次落回工作檯上那流轉著生命光澤的盤面,「美,不該因為一點傷痕就被徹底否定。」
鹿港冬夜特有的鹹濕海風,從門縫裡絲絲縷縷地鑽進來,帶著低沉的嗚咽。工作室裡,只有陳姐手中鑷子尖端偶爾碰觸金屬發出的、細微如嘆息般的聲響。她開始了魔法般的拼裝。
她捨棄了那枚雖然輕薄但規格並不完美匹配的 NH05A 機芯,轉而從身後牆壁無數的零件格中,精準地挑選出幾枚來自不同「遺骸」的部件:一枚老舊但走時尚穩的精工女錶機芯(Cal. 4205)的主夾板;幾枚來自西鐵城機芯的齒輪;一根斷裂後被重新修復的發條……她的動作流暢而充滿韻律,像一位編織時光的詩人。鑷子與螺絲刀在她手中彷彿有了生命,精準地將這些來自不同「屍骸」的器官,天衣無縫地組合在一起,構成了一顆獨一無二、帶著歷史傷痕卻依然有力跳動的「心臟」。
接著是錶殼。那枚28mm的鋼殼,邊緣的凹痕她沒有試圖完全打磨掉,只是用極細的拋光棒小心地處理了最尖銳的毛刺,讓傷痕變得溫潤,成為錶殼歷史的一部分。然後,是最關鍵的一步——裝載那枚帶著裂痕的貝母盤。
她先用特製的、極其柔軟的無塵布,蘸取微量專用清潔液,以近乎呵護的輕柔力道,一遍遍擦拭著盤面。那道細長的裂痕在檯燈下無所遁形,像一道凝固的閃電,又像美人臉頰上未乾的淚痕。虹彩在清潔後愈發流動奪目,裂痕的存在,非但沒有削弱它的美,反而增添了一種破碎後重生的、驚心動魄的真實感。她調配了一種幾乎透明的專用黏合劑,用比髮絲還細的點膠筆,小心翼翼地將極微量的膠水點在錶殼內圈對應盤面裂痕下方的幾個支撐點上。每一個動作都屏息凝神,精確到微米。她沒有試圖填補或掩蓋那道裂痕,只是確保它能被穩固而平貼地支撐在錶殼之中。
當貝母盤被穩穩地安放妥當,虹彩在燈光下靜靜流淌,那道裂痕也成為整體美感的一部分時,陳姐輕輕舒了一口氣。她拿起那枚鑲嵌著廉價水鑽的三角坑紋外圈。水鑽在燈下折射出略顯浮誇的七彩光芒,與貝母盤那內斂而多變的天然虹彩形成了微妙對比。她將外圈對準錶殼,手腕穩定下壓,精準的「咔嗒」一聲,外圈嚴絲合縫地歸位。廉價的水鑽,華麗的貝母,破碎的痕跡,在這一刻奇異地融合為一個整體,矛盾卻和諧。
最後是指針。她沒有使用原配的,而是挑選了三根纖細的藍鋼指針——時針和分針來自一塊報廢的老歐米茄蝶飛,秒針則來自一枚早已停產的浪琴女錶。她將它們一一安裝到機芯的軸上。當鑷子鬆開秒針尾端,那根纖細的藍鋼針,開始了它新的旅程,在流動的貝母盤面上,穩定地、順滑地掃過每一個鑲嵌著水鑽羅馬數字的時標。沒有絲毫卡頓,沒有半分遲疑。
不知何時,屋外連綿的冬雨竟悄然停歇。厚重的雲層裂開了一道縫隙,清冽的月光,如同被洗淨的銀練,透過工作室狹窄的氣窗,不偏不倚地傾瀉而下,正好籠罩在陳姐剛剛完成的這枚拼裝腕錶上。
銀輝流淌。貝母盤上那天然的虹彩,在純粹的月光下被徹底喚醒,深藍的底色彷彿化為幽靜的深海,紫羅蘭、墨綠、碎金的紋路在月華中無聲湧動、變幻,美得令人窒息。那道細長的裂痕,在清冷的光線下,像一道凝結的冰紋,又像通往另一個夢幻維度的神秘入口。鑲嵌在廉價外圈上的水鑽,此刻也褪去了白熾燈下的浮華,折射出點點清冷如寒星的微光。三根藍鋼指針,在月光下泛著幽邃而沉靜的藍暈,如同在深海中優雅巡遊的精靈。整個錶盤,在這一刻彷彿擁有了生命,在月光的撫觸下靜靜呼吸。
陳姐沒有說話。她只是靜靜地凝視著這枚在廢墟中重生、在月光下綻放的作品。她的指尖,帶著長期與金屬油污打交道的薄繭,極其輕柔地拂過冰冷的錶殼,最終停留在錶鏡邊緣,那道來自貝母盤本身的、無法被修復的細微裂痕之上。她的動作充滿了難以言喻的憐惜與理解。
「碎掉的東西,」她的聲音很輕,像怕驚擾了月光下流動的虹彩,卻清晰地落在這寂靜的空間裡,「有時反而能拼出真模樣。」她的目光沒有離開那道裂痕,彷彿透過它,看到了更深遠的東西,「工廠裡,只看見它裂了,廢了,不值錢了。可在我這裡,」她抬起眼,目光沉靜地看向我,「這道裂痕,讓它成了獨一無二的那一片貝母。讓它不再是流水線上一個冰冷的零件編號。它的美,因為這道傷,反而有了來處,有了故事,有了……真的溫度。」她的指尖感受著那道裂痕細微的起伏,「就像人,摔過,痛過,裂過,縫補起來的痕跡裡,藏著的才是真滋味。光溜溜、完美無缺的,」她微微搖了搖頭,嘴角浮起一絲看透世情的淡然笑意,「那多半是假的。」
月光靜靜地流淌在「時光邊角」的工作檯上,籠罩著那枚奇蹟般的拼裝腕錶,也照亮了陳姐眼角細密的皺紋和眼中沉澱的智慧。我看著眼前這一切,想起老周枯槁手指下藏匿的真表冠,想起基隆港查獲的十億完美的高仿手錶,想起批發市場裡為了蠅頭小利爭執的面孔,想起金融風暴下林老闆工廠裡熬夜打磨殼型的師傅們……台灣鐘錶業這條漫長而曲折的灰色鏈條上,承載了太多生存的掙扎、技術的偏執、對「真」的畸形渴望與對「假」的靈活利用。而在這條鏈條最不起眼的末端,在這鹿港幽深的小巷盡頭,一位被主流拋棄的女匠人,卻用她沾滿油污的雙手和洞悉世情的雙眼,在無數被丟棄的「殘骸」中,在那些不被認可的「瑕疵」與「裂痕」裡,拼湊出了一種超越真偽標籤的、更為本真的存在價值。
離開「時光邊角」時,月光已鋪滿濕漉漉的紅磚巷弄,清冷皎潔。我下意識地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自己那隻功能精準、外觀無瑕的正裝錶。冰冷的金屬錶殼反射著月華,完美,卻也冰冷。陳姐的話語,像鹿港深夜帶著鹹味的風,繚繞不散。當追求完美的執念成為枷鎖,那道月光下靜靜流淌的裂痕,反而成了叩問真實的印記。原來所謂真偽,有時不過是人間煙火烙在時光肌理上的紋路,在生存的夾縫裡,透出微弱卻頑固的、屬於人的溫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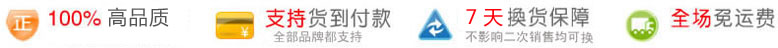
 LINE關注
LINE關注
